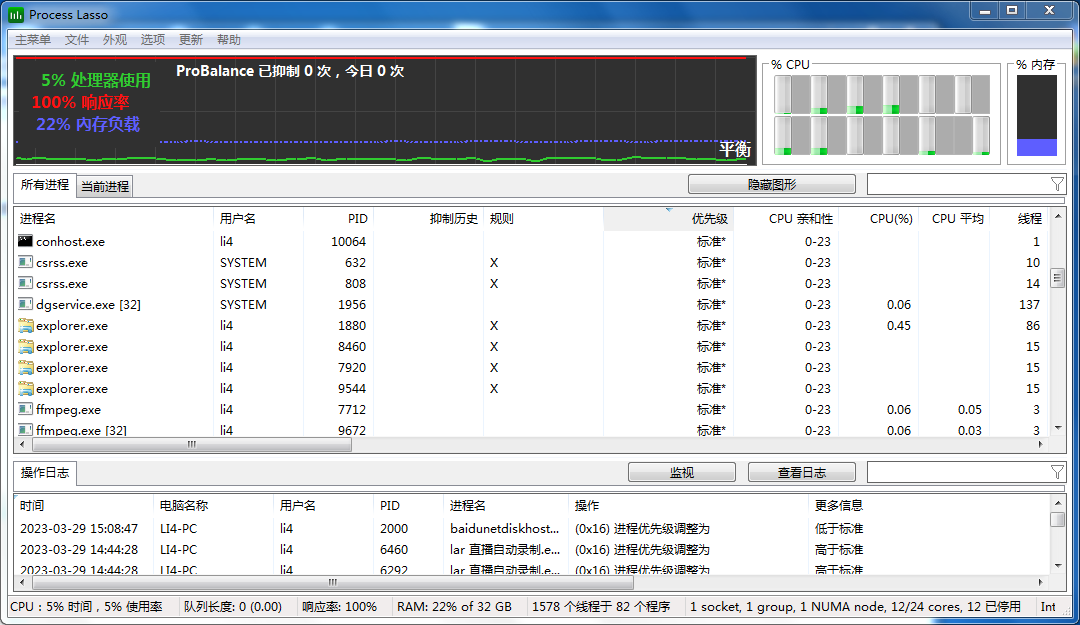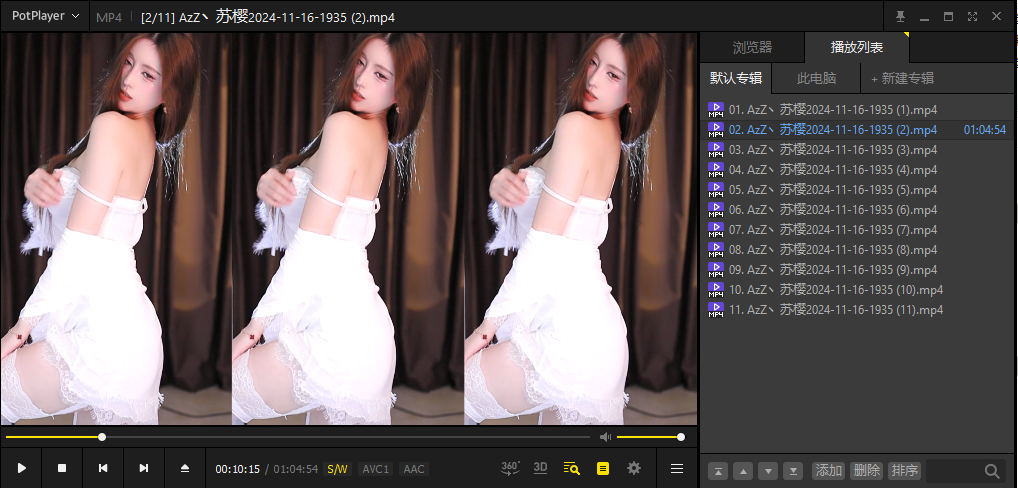文|韩淑霞
想起儿时过年的情景,仿佛有一层水雾缓缓漫起,触动了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。分明已经很遥远,却又仿佛发生在昨天,朦胧而又美好。
过年最深刻的记忆,自然是包除夕夜的饺子。裹着小脚的曾祖母常念叨:“腊月三十晚上吃素馅饺子,是祖辈上传下来的规矩,讲究的是一年素素净净,顺顺当当,不生闲气。”
母亲往往会挑选上好的韭菜,洗净,细细切了,撒上事先炒好的鸡蛋屑,再佐以盐、香油、五香面等调料调匀。韭菜青绿如玉,蛋屑点点似碎金,两者搭配相得益彰。微辣中伴着鲜香扑面而来,充溢整个房间,堪称色香味俱佳。
我总是爱黏在母亲身后,年三十的饺子要敬神祭祖,马虎不得,母亲担心我捏不紧,煮破了不好看,不许我动手包,只让帮着按剂子。不过,这丝毫不影响我的兴致,我常常踮起脚来,几乎用上全身的力气,把每个剂子都按得圆圆的,扁扁的。
“霞儿中用了,能帮忙了,”这时,母亲总爱乐呵呵地夸一句。此时的我像得到了无上的奖赏,心里美美的,像盛满了蜜糖。
包饺子工作接近尾声,父亲端着母亲提前熬制好的浆糊儿,要去贴对联。他一手拿着扫帚,一手端着小锅招呼:“霞儿,和我去贴对联。”
“好来!”我洗洗手,搬上小板凳,抱上对联,一路小跑乐颠颠地追着父亲。
父亲先撕去往年的对联,扫净门框上的浮尘,再贴新的。这时候,我把两条对联展开,父亲看看这边,又看看那边,自言自语:“先贴那个呢?”犹豫片刻,念一念,不外乎是“去年已是十分好,今岁更上一层楼”,也有“向阳门户春常在,吉祥人家庆有余”之类。父亲果断地大声说:“啊,这个吧!”
我便递上去。不一会儿,对联贴好了。红艳艳的对联衬着,小院里节日的喜庆气氛愈发浓厚。
父亲把正屋坐北朝南的条桌擦得干干净净,把家堂请出来,工工整整挂在桌子正上方。我在一旁看着:只见上面画着一座楼,每层楼中间画着小格子,格子中间有字。我问父亲:“这是什么?”
父亲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,他温和而又郑重地告诉我:“这是咱们的祖先,小格子里写着他们的名字!”
我痴痴地望着家堂,暗自想:这么多人挤在一层楼里,每个格子差不多和我的一个手指肚一样宽,祖先们在里面会不会太挤?会不会挤得慌?噢,他们好辛苦!
天色渐渐暗下来,黄昏时分,父亲随同院中的男人们一起去请“爷爷娘娘”。所谓的请“爷爷娘娘”,就是春节把逝去的亲人们请回家。这是我们鲁西北农村过年的风俗习惯,也是春节期间最重要、最隆重的活动内容之一,代代相传,年年如此。
这项习俗究竟起源于何年何代,已无从考证。现在想来,人们是借此祭祖,以增强家族观念,表达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祈盼吧。
此时,母亲把各种供品一一摆好,方形的猪肉、红公鸡、鱼、各色炸货、干鲜果品……可称得上是应有尽有。
摆好供品后,父亲也回来了,放好“拦门杠”。
“拦门杠”就是一支木杠,长度要达到自己大门口那么宽,据说这样可以挡住别人家的神来自己家过年。看看供桌上,父亲觉得似乎少了什么,就吩咐我拿过几本书放到桌上。我很奇怪:难道先祖们也要读书吗?后来才明白:父亲希望先祖们能保佑下一代学业有成。曾祖母在一旁反复嘱咐:“别大声说话,不要打喷嚏,不然祖宗们会怪罪的。”
口头上应着,我悄悄问大姐:“万一忍不住怎么办?”姐姐说:“揉揉鼻子啊,就能忍住。”噢,还是大姐有经验,我暗想。
父亲把全家人都叫过来,恭恭敬敬地烧纸上香磕头,烟雾缭绕中,奶奶带领我们虔诚地叩拜,满满的仪式感。
晚饭后,母亲笑盈盈地拿出新衣服,挨个给我们试穿。家里五个孩子,人手一套。这是从入夏天以来,母亲就开始准备的,这是她辛苦了大半年,不知熬了多少夜的杰作。此刻,她给这个拽拽袖子,给那个抻抻裤角,姐妹们个个眉开眼笑,其乐融融。
仪式完毕,坐看春晚,欢天喜地守岁,只待迎接新春的钟声敲响。可惜这样的年,一去不复返了!
如今,我已近天命之年,常感“物是人非事事休”,只觉得年味越来越淡。有人说:“不是年味淡了,而是我们都长大了。”即便如此,我还是期待过年。因为只有过年,一家人才能一起吃团圆饭、聊天谈心,和和美美,共享静好岁月。纵使繁华落尽,我心依然存有余香,仍有一脉烛火在记忆中跳荡,温暖余生。让我依然能在每年的这个时刻,在冬的余威里,向往春天!
作者简介:韩淑霞,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,德州市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诗歌网认证诗人。诗文刊登于“学习强国”平台、《山东散文》《山东诗歌》《辽宁青年》《山东工人报》《农村大众》《散文选刊》等。